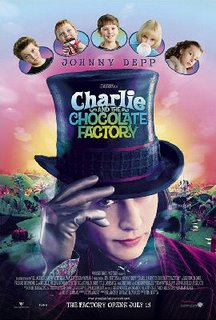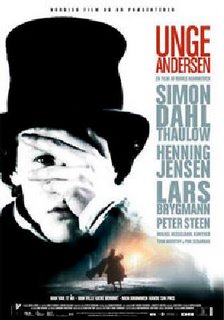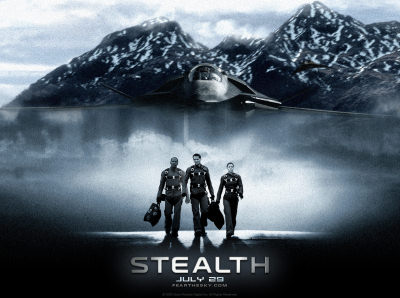「色計」(Anthony Zimmer)
 Sophie Marceau的美,不在年輕,而在神韻。在這部法國驚悚懸疑片中,Sophie飾演美女Chiara,為抓到洗錢高手Anthony Zimmer以身為餌。Anthony Zimmer據說時常易容變身,沒有人看過他的真面目,Chiara是他最愛的女孩,法國警察Akerman於是想利用Chiara誘捕Anthony。
懸疑片之所以懸疑,在於劇情進行中只揭露一部份的事實,故意隱藏了真相。其貌不揚的Francois,以夫妻不合獨自出外旅行的姿態出現在火車裡,Chiara看上了他,一付找人陪伴的有錢貴婦模樣,讓Francois體驗到富有的生活。其實Chiara把Francois識為Anthony Zimmer,因此故意接近他。
之後Francois陷入被追殺的危機中。這樣子的開場,Francois像一個無端惹來殺身之禍的無辜民眾,Chiara也對他感到抱歉,只得安排他到安全的地方小住。
不過Francois不甘處於被保護的角色,因為他愛上Chiara,他想要保護身為誘餌的Chiara的安全。
一切是那麼合理,只是Anthony Zimmer還未現身,不知身在何處。根據線報,警方在Anthony可能出現的山中豪宅中,佈署重兵包圍,Chiara再度身負重任,隻身深入豪宅一探究竟。劇情的詭譎在此,Francois偷進豪宅想維護Chiara的安全,同時Anthony Zimmer也進入了豪宅。到底Anthony的廬山真面目為何,觀眾與我一樣都急迫地想要看到。
當發現誤認Francois為Anthony後,警方及Chiara一方面會產生愧疚心態,另一方面有任何新線索都不再懷疑他,對他的判斷自然有失正確。這樣的心理伴隨著觀眾,當Francois在Chiara耳邊說出真相時,勢必跟Chiara一樣驚奇不已。真有眾裡尋她千百渡,伊人卻在燈火欄跚處的感嘆。大膽的Anthony Zimmer做出正確的判斷,Chiara最終並沒有把真相告知警方,Anthony仍舊來無影去無蹤,仍舊沒有人看過他的真面目。本片是警察捉強盜,但重點不在正義的實現,而在你來我往的鬥智,虛實之間的巧妙安排,畢竟片中沒有強調洗錢高手做了甚麼壞事。
設計他人的人反被設計,道高一尺魔高一丈,看得觀眾眼花撩亂。計計之中真假難辨,誰被耍了?是的,法國警方被耍了,但觀眾才真正被耍得團團轉。
Sophie Marceau的美,不在年輕,而在神韻。在這部法國驚悚懸疑片中,Sophie飾演美女Chiara,為抓到洗錢高手Anthony Zimmer以身為餌。Anthony Zimmer據說時常易容變身,沒有人看過他的真面目,Chiara是他最愛的女孩,法國警察Akerman於是想利用Chiara誘捕Anthony。
懸疑片之所以懸疑,在於劇情進行中只揭露一部份的事實,故意隱藏了真相。其貌不揚的Francois,以夫妻不合獨自出外旅行的姿態出現在火車裡,Chiara看上了他,一付找人陪伴的有錢貴婦模樣,讓Francois體驗到富有的生活。其實Chiara把Francois識為Anthony Zimmer,因此故意接近他。
之後Francois陷入被追殺的危機中。這樣子的開場,Francois像一個無端惹來殺身之禍的無辜民眾,Chiara也對他感到抱歉,只得安排他到安全的地方小住。
不過Francois不甘處於被保護的角色,因為他愛上Chiara,他想要保護身為誘餌的Chiara的安全。
一切是那麼合理,只是Anthony Zimmer還未現身,不知身在何處。根據線報,警方在Anthony可能出現的山中豪宅中,佈署重兵包圍,Chiara再度身負重任,隻身深入豪宅一探究竟。劇情的詭譎在此,Francois偷進豪宅想維護Chiara的安全,同時Anthony Zimmer也進入了豪宅。到底Anthony的廬山真面目為何,觀眾與我一樣都急迫地想要看到。
當發現誤認Francois為Anthony後,警方及Chiara一方面會產生愧疚心態,另一方面有任何新線索都不再懷疑他,對他的判斷自然有失正確。這樣的心理伴隨著觀眾,當Francois在Chiara耳邊說出真相時,勢必跟Chiara一樣驚奇不已。真有眾裡尋她千百渡,伊人卻在燈火欄跚處的感嘆。大膽的Anthony Zimmer做出正確的判斷,Chiara最終並沒有把真相告知警方,Anthony仍舊來無影去無蹤,仍舊沒有人看過他的真面目。本片是警察捉強盜,但重點不在正義的實現,而在你來我往的鬥智,虛實之間的巧妙安排,畢竟片中沒有強調洗錢高手做了甚麼壞事。
設計他人的人反被設計,道高一尺魔高一丈,看得觀眾眼花撩亂。計計之中真假難辨,誰被耍了?是的,法國警方被耍了,但觀眾才真正被耍得團團轉。
「翻滾吧!男孩」(Jump! Boys)
 近年來民風漸開,紀錄片受到民眾較多的注意。在商業電影恆大的主流市場中,紀錄片要熬出頭,得靠不凡的拍攝標的與過人的描述手法,才能獲得大眾的認同。在本土社會找題材的紀錄片,本來就不多,也許大眾關心的是其他「更高層次」的問題,但這樣的題材若運用得當卻較易喚起觀眾的共鳴,因為它可能是在你我身旁的普通人、普通事。
以小學體操隊為題材,最初的想法是「那有甚麼好演的」。導演林育賢會以宜蘭公正國小體操隊為標的,拍攝教練與小小選手們的訓練與生活狀況,原因是「近水樓台」,教練林育信是導演的哥哥。導演藉由哥哥工作之便,隨隊參與訓練過程,捉取每個小選手的個性與喜怒哀樂,深入小選手家庭探討家長與親友的態度,直到全隊參加年度全國體操競賽,記錄成功獲獎的那一刻。
台灣小孩在長久的升學主義影響下,走理工文財法醫被視為正途,其他方面都被視為「書唸不好」而不得不走的「備案」,家長多半不抱希望。體育運動屬於此類,體操更被視為沒有前途,會害孩子長不高的運動,至少教練林育信小時成長環境是如此看待。那麼這群練體操的小學生,是家長的支持?還是小學生自己的喜好?本片中可以看到家長的態度,及小男孩們對體操運動「愛恨交織」的矛盾心理。
黃克強、李智凱、楊育銘、林信志、黃靖、以及小軒與小恩,這七個從小學二年級到幼稚園大班都有的小小選手,怕教練的兇,怕壓筋、摔跤受傷的痛,幾乎每個人都因此哭過,並非不曾萌生退意,只是由於各種原因,他們繼續在體操隊待了下來。國小低年級學生,打鬥吵鬧是天性,哭笑等情感的劇烈變化也是上天賦予。導演將這群小學生學業、生活、交友等除了訓練以外的細節,成功地展現給觀眾,讓我們知道這群小男孩就像一般同年級小學生一樣,除了體操,沒有特別強或特別出眾之處。當校長授旗參加全國競賽,這群男孩們從當初訓練時隨時感到緊張,到比賽前個個口中都說不會緊張,看得出他們對自己這一年來的所練所學,獲得一定程度的自信。當然,教練更為臭屁。
2003年在高雄舉辦的全國比賽,他們獲得低年級組全國冠軍,決非偶然。比賽中,有選手演出失常,也有選手表現超水準,對年紀尚輕的小男孩而言,穩定性是最難維持的。記得那個幼稚園大班的小恩嗎?常因每周模擬競賽總是最後一名而哭泣,鞍馬項目只有轉一圈的能力,被戲稱為「牛奶糖」。後記在一年後(2004年)的全國比賽中,再度看到公正國小體操隊的身影,此時的小恩已非昔日阿蒙,翻滾跑跳樣樣行,鞍馬自然是連續動作毫不含糊,成為一個真正的體操小選手,相信他已擺脫最後一名的宿命。努力,就有收穫,我們看到感人的真實案例。
體操競技在台灣,屬非常冷門的運動,我們看到這一小撮人,儘管來自各種不同的小康家庭,家長的態度與小朋友的個性各異,他們為共同目標一起努力前進的團隊精神令人敬佩。導演以身旁的事物為題材,因為熟悉,所以感人,可為紀錄片成功的典範。
近年來民風漸開,紀錄片受到民眾較多的注意。在商業電影恆大的主流市場中,紀錄片要熬出頭,得靠不凡的拍攝標的與過人的描述手法,才能獲得大眾的認同。在本土社會找題材的紀錄片,本來就不多,也許大眾關心的是其他「更高層次」的問題,但這樣的題材若運用得當卻較易喚起觀眾的共鳴,因為它可能是在你我身旁的普通人、普通事。
以小學體操隊為題材,最初的想法是「那有甚麼好演的」。導演林育賢會以宜蘭公正國小體操隊為標的,拍攝教練與小小選手們的訓練與生活狀況,原因是「近水樓台」,教練林育信是導演的哥哥。導演藉由哥哥工作之便,隨隊參與訓練過程,捉取每個小選手的個性與喜怒哀樂,深入小選手家庭探討家長與親友的態度,直到全隊參加年度全國體操競賽,記錄成功獲獎的那一刻。
台灣小孩在長久的升學主義影響下,走理工文財法醫被視為正途,其他方面都被視為「書唸不好」而不得不走的「備案」,家長多半不抱希望。體育運動屬於此類,體操更被視為沒有前途,會害孩子長不高的運動,至少教練林育信小時成長環境是如此看待。那麼這群練體操的小學生,是家長的支持?還是小學生自己的喜好?本片中可以看到家長的態度,及小男孩們對體操運動「愛恨交織」的矛盾心理。
黃克強、李智凱、楊育銘、林信志、黃靖、以及小軒與小恩,這七個從小學二年級到幼稚園大班都有的小小選手,怕教練的兇,怕壓筋、摔跤受傷的痛,幾乎每個人都因此哭過,並非不曾萌生退意,只是由於各種原因,他們繼續在體操隊待了下來。國小低年級學生,打鬥吵鬧是天性,哭笑等情感的劇烈變化也是上天賦予。導演將這群小學生學業、生活、交友等除了訓練以外的細節,成功地展現給觀眾,讓我們知道這群小男孩就像一般同年級小學生一樣,除了體操,沒有特別強或特別出眾之處。當校長授旗參加全國競賽,這群男孩們從當初訓練時隨時感到緊張,到比賽前個個口中都說不會緊張,看得出他們對自己這一年來的所練所學,獲得一定程度的自信。當然,教練更為臭屁。
2003年在高雄舉辦的全國比賽,他們獲得低年級組全國冠軍,決非偶然。比賽中,有選手演出失常,也有選手表現超水準,對年紀尚輕的小男孩而言,穩定性是最難維持的。記得那個幼稚園大班的小恩嗎?常因每周模擬競賽總是最後一名而哭泣,鞍馬項目只有轉一圈的能力,被戲稱為「牛奶糖」。後記在一年後(2004年)的全國比賽中,再度看到公正國小體操隊的身影,此時的小恩已非昔日阿蒙,翻滾跑跳樣樣行,鞍馬自然是連續動作毫不含糊,成為一個真正的體操小選手,相信他已擺脫最後一名的宿命。努力,就有收穫,我們看到感人的真實案例。
體操競技在台灣,屬非常冷門的運動,我們看到這一小撮人,儘管來自各種不同的小康家庭,家長的態度與小朋友的個性各異,他們為共同目標一起努力前進的團隊精神令人敬佩。導演以身旁的事物為題材,因為熟悉,所以感人,可為紀錄片成功的典範。
「最好的時光」(Three Times)
 侯孝賢的電影,有時不是很容易懂,但其 實大多數的時候,是觀眾把電影想得太複雜了,以為偉大的電影一定要有偉大的意涵,而且要隱藏在「表面」之下。當導演導的片越來越多,成就受到大眾肯定,自 然開始想拍屬於「自己」的東西。電影都會有劇情,劇情的存在有時為了展現一個故事的來龍去脈,有時為了培育一種氣氛。這種氣氛感動了觀眾,電影就算成功。
侯孝賢的電影,有時不是很容易懂,但其 實大多數的時候,是觀眾把電影想得太複雜了,以為偉大的電影一定要有偉大的意涵,而且要隱藏在「表面」之下。當導演導的片越來越多,成就受到大眾肯定,自 然開始想拍屬於「自己」的東西。電影都會有劇情,劇情的存在有時為了展現一個故事的來龍去脈,有時為了培育一種氣氛。這種氣氛感動了觀眾,電影就算成功。
台灣近百年的歷史,由於政治因素,主軸 常是非本地人的觀點,對於市井小民,誰當國王皇后並不是最重要的事。民眾的生活回憶,在於工作、生活、感情的點點滴滴,這些融合成為對時代的觀感。美好的 回憶,不是一段長時間的幸福,往往是短時期的片刻時光。我們心中對自己成長過程的美好記憶,是否常是某一個事件,或某一段特定時期呢?
侯氏在本片展現的美好時光,按順序分別於戀愛夢、自由夢與青春夢中呈現。第一段故事年代在1966年的雲嘉地方小鎮,第二段在1911年 台北大稻埕,第三段則是現代的台北縣。三個年代,三段情緣,男女主角都由舒淇與張震擔綱。第一段是目前四、五十歲以上民眾熟悉的成長環境,在美蘇冷戰反共 抗俄仍喊得震天響的台灣農村,純樸的社會年輕男女有著純樸的愛,一切是那麼簡單、自然,雖然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會覺得當時的男女都很ㄍㄧㄥ,不過就是ㄍㄧㄥ 才產生了期待,幻化出美麗的憧憬。當時台灣國片的主流以愛情文藝為主,多少說明了那是個適合「談戀愛」的時代。
第二段拉到很久遠的時代,是辛亥革命前 的日治時期,當時台北繁華之地屬大稻埕、萬華與城內所圍的區域。故事以藝旦與文人來往為背景,藝旦對自由的心願,需有心人願意出錢贖身得以嫁為人婦;文人 士紳對自由的追求則在於讓台人脫離日人統治,以及在中國建立新政府的渴望。身份差異大的男女,對自由的定義完全不同,只是何時得以實現?藝旦的心願,文人 男子無言以對;男子的心願,也只有天才曉得。這段比較特殊的是,為了解決語言問題,全部以默劇形式演出,觀眾就像旁觀者般,靜靜觀察角色間的互動。
第三段拉回現代,是年輕人的世代。在激 情狂野與三角關係中,建構青春蓬勃的氣息。時代是沒有錯的,沒有人能控制時代的走向,在這個屬於年輕人的青春夢裡,我們看到難解的情愛關係。時間會繼續往 前進,再怎麼難解的習題總有解決或消失的一天,年輕充滿無限可能,是美好的世代。把現代視為美好的時光之一,也讓本片多了些許勵志成份。
前後跨越近百年,每段時光都充滿了當時的環境元素,讓我們回味無窮。時代的移轉扯動所有人事物的變遷,只有相隔幾十年才感覺到明顯差異。以侯氏的眼光來看有他認知的美好時光,那你呢?你認知的美好時光又在何時?何處?
「王者天下」(Kingdom of Heaven)
 這部像史詩般的中世紀電影,以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前的聖地耶路撒冷為背景,描述一個懷有理想的偉大騎士,是如何維護和平、保衛國家人民,為建立心目中的天堂之國努力不懈。
這部像史詩般的中世紀電影,以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前的聖地耶路撒冷為背景,描述一個懷有理想的偉大騎士,是如何維護和平、保衛國家人民,為建立心目中的天堂之國努力不懈。
西元1186年前後,三教聖地耶路撒冷由基督教的Baldwin王統治,Saladin統領強大的回教軍隊意圖將聖城奪回。Orlando Bloom飾演的Balian原是法國一名鐵匠,也是Baldwin王麾下騎士團長Godfrey的私生子。Balian跟隨父親來到耶路撒冷,接任父親的爵位與領地,懷抱遠大理想的他,夢想建立一個和平的天堂之國,在那裡基督教徒、猶太教徒與回教徒和平共處,過著幸福的生活。只是事與願違,真實的情況總是挫折不斷。
Balian拒絕娶Baldwin的妹妹Sibylla,並接任為耶路撒冷的國王,儘管他心中與她相愛,但Sibylla原已準備嫁給另一位騎士Guy de Lusignan,Balian為道德與避免宮廷內部爭鬥而不願從中破壞。Guy de Lusignan是一位聖殿騎士,聖殿騎士是最不願與回教徒妥協的一群,屬於基本教義派,他娶了Sibylla成為國王,也為原本脆弱的和平帶來毀滅性的結果。
好戰的Guy de Lusignan主動出戰領有20萬回教大軍的Saladin,戰敗被俘後,耶路撒冷國已經岌岌可危,愛好和平的Balian不得不帶領僅剩的老弱殘兵,為保護他的人民做最後一搏。以少數兵力使盡全力防守,博得敵人Saladin的尊重,Balian終於做出最後最適當的選擇,決定和平讓出耶路撒冷,保證其子民的人身安全。自此回教徒再度掌控聖城,直到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基督徒仍舊無法將聖城奪回。
面對這段史實,不得不懷疑這難道不是上帝開的玩笑?一個小城耶路撒冷陰錯陽差成為猶太教、基督教與回教的聖域,導致近兩千年該地區的紛爭不斷,戰火頻仍。不論穆罕默德或耶穌基督,其在天之靈真的會希望他的子民為此互相砍殺,死傷無數,只為搶奪聖城?難道前後長達200年的十字軍東征歷史,始作俑者竟是一項烏龍?
西洋中世紀的騎士,被賦予懷著崇高理想,為正義與和平努力奮鬥的完美武士。這麼一個正義的化身,能夠做到並讓後世稱頌的偉大騎士並不多。Balian的事蹟因年代久遠,也許有些穿鑿附會,不過他代表的形象,正是現代社會缺乏的典範。這樣的移情作用,不正也說明現代社會普遍的期盼嗎?
「世界大戰」(War of the Worlds)
 改編自H.G. Wells同名的經典科幻小說,加上Steven Spielberg 執導與Tom Cruise主演,這部片一開拍就註定了它的長相。War of the Worlds的Worlds,複數暗示了兩個不同世界間的戰爭。人類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與生俱來,浩瀚無垠的宇宙誰能保證不存在其他文明,若存在外星文明誰又能保證不會與人類發生武力衝突?
改編自H.G. Wells同名的經典科幻小說,加上Steven Spielberg 執導與Tom Cruise主演,這部片一開拍就註定了它的長相。War of the Worlds的Worlds,複數暗示了兩個不同世界間的戰爭。人類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與生俱來,浩瀚無垠的宇宙誰能保證不存在其他文明,若存在外星文明誰又能保證不會與人類發生武力衝突?
本片不從因果推論來導引星際戰爭的發生,而是以一個再普通不過的碼頭工人Ray的角度,來看待外星人奇襲地球的戰爭。外星人不知從何而來,進攻方式也令人意想不到,因為外星武器早就埋在地表深處,可能地球尚未有人類出現前就埋下去了。而密集得不可思議的閃電,是外星人從天而降通往地底武器的軌道,外星人開動三隻腳的尖端武器,破土而出,大肆破壞。Ray面對突如其來的毀滅攻擊,唯一的責任是盡全力保護兒子與女兒的安全,執行一個做爸爸的職責。
當人們面對滅絕式侵犯,激發出求生存的動物本能時,會怎麼做?是孤注一擲做出反擊,以求一線生機;還是隱忍不發,全力逃亡?Ray的兒子與收留他的朋友無疑選擇前者,但Ray則選擇後者。兩種看法的衝突,在以求生為第一目標下,所有道德規範全被捨棄,我們看到的是赤裸裸的自私掠奪和自相殘殺。拯救你的人,不必報恩,更要殺害他掠奪他所有的物品。此時,誰最心狠手辣,誰就是最後的生存者;仁慈與寬恕,是壞事的最大根源,務必除盡。
在外星武器的毀滅性攻擊下,人們很難獲得新聞資訊,對戰況的瞭解也就道聽塗說。Ray跟一般民眾一樣,眼之所見即為所有認知,他看到三隻腳武器突然失去防護,他也看到他們一個個莫名其妙倒下,任美軍反擊宰割,終於地球在這場外星戰役中意外地獲得最後勝利。雖然,民眾當時在缺乏資訊下並不知何以得勝。
微生物、病毒、細菌,做為地球的一份子,跟人類 一樣有職責保衛地球,而他們發揮最大功效,以感染的方式給外星生物致命一擊。以現在來看這雖有點老套,不過以原著的年代而言這卻是最巧妙的結果。寓意在 於,地球生命不論高低階層,已構成關係緊密的巨大生態圈,生物間互相依存,鏈結複雜。人類討厭帶來疾病的各式病毒,但病毒卻在「世界大戰」一役中拯救人類 免於滅種,也拯救了地球。也許人們該思考對待地球環境的方式,畢竟地球只有一個,沒多的了。
「野戀情挑」(Le Festin de la Mante; The Praying Mantis)
 母螳螂與公螳螂交合後,母螳螂將公螳螂吃掉的昆蟲知識,被活生生搬上大銀幕。這部獲得多國影展獎項,如聖荷西國際影展、舊金山國際影展、布魯塞爾國際奇幻電影節等,猶如大膽狂野的人類性愛觀察。當愛情無法滿足野獸般的性慾需求,誰將是受害者?
母螳螂與公螳螂交合後,母螳螂將公螳螂吃掉的昆蟲知識,被活生生搬上大銀幕。這部獲得多國影展獎項,如聖荷西國際影展、舊金山國際影展、布魯塞爾國際奇幻電影節等,猶如大膽狂野的人類性愛觀察。當愛情無法滿足野獸般的性慾需求,誰將是受害者?
Sylvia與大提琴家Julien在法國南部鄉間生活,Julien熱愛著太太Sylvia,讓Sylvia擁有自己的溫室,親手照顧溫室中的一草一木。只是當今夏一波熱浪襲來,潛藏在Sylvia體內不為人知的狂野,對性與殺害伴侶的強烈需求,從隱性展為顯性。但Julien對她的愛令她無法對丈夫下手,只好勾引浪子第三者Patrick投網。撞見太太與Patrick在閣樓交歡的Julien,在氣憤之餘,終於瞭解到Sylvia真正的需求,而主動要求Patrick來此與其妻媾合。這是一幕多麼不協調的畫面,親友們指指點點,百思不得其解。
在閣樓上Julien與Patrick跳起求愛之舞,集合藝術與浪漫,擺弄優美的性愛肢體,相信是本片的精華片段,不得不佩服法國人(本片為比利時出品)在這方面的功力。不僅如此,當片尾兩人在溫室裡跳起最後一支性舞,Julien挺著大提琴為他們伴奏之際,像是死亡前最後的美麗,母螳螂在獲得高潮後的致命一擊,無聲而夢幻,一切在百分百的完美下迅速歸零,劃下句點。Julien奉獻最大的愛,讓情人獲得滿足;大愛將穿越時空,在從前與未來的某個時刻裡,重覆不斷母螳螂殺死公螳螂的戲碼,Julien對此無怨無悔,但求完美。
法國一帶的人們對性愛的觀點較為開放,探討直接而露骨,從片中可窺一二。性原是動物本能,動物演化史從無性生殖發展出有性生殖後,區分公母、雄雌、男女的模式,就註定了交合的必然性與重要性。若生命是以延續生命為主要目的(現在看來是這樣),那麼包括人類在內,性交將是個體在生與死之間最重要的事件。性的生物目的在製造生命,而殺害則在毀滅生命,若說凡事正反是一體兩面,交合後殺死伴侶的潛在慾望,是否是平衡生命狀態的可能現象?若果,你我心中都潛藏著類似基因,可不驚駭?
「巧克力冒險工廠」(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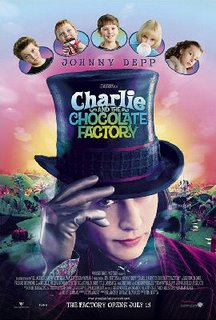 改編自Roald Dahl著名的童話故事,「巧克力冒險工廠」捨棄一般電影的寫實風格,以創造一個神秘的童話世界為目標,讓觀眾悠遊於奇幻的巧克力工廠中,由Johnny Depp飾演的廠長Willy Wonka帶領,在神奇的工廠中展開冒險旅程。
好的童話故事能將教育內容嵌入故事情節中,在本片以五個抽到Golden Tickets的小孩,得以進入神秘工廠一探究竟為由,在參觀的過程中寓教於樂,算是適得其所。這五個小孩,有的很愛吃,有的被寵壞,有的很高傲,有的沉迷於科技世界,當然也有一個家雖貧窮卻珍惜家庭生活的小孩,名叫Charlie。從Charlie的爸媽及爺爺,為了實現Charlie夢想抽到Golden Ticket的願望而購買昂貴的Wonka巧克力,最後雖然失望而回,但知足的Charlie從不怨天尤人,可看出這三代人擠在一間小木屋中的溫暖與幸福。終於幸運之神降臨,Charlie抽到夢寐以求的Golden Ticket,得以和其他個性各異的四個小孩進入巧克力工廠內參觀。
既是童話,不能有人死亡。在奇怪的Willy Wonka帶領下,四個小孩分別因為個性上的缺失而出事,有的掉入巧克力池、有的變成大藍莓、有的掉入深淵、有的縮成姆指姑娘一般小,但這些孩子都不會致死,只是變成各種奇怪模樣作為懲罰。家長陪著孩子一起受罪,多少象徵著孩子的管教職責在於家長的意味。除了孩子之外,廠長Willy Wonka也在與Charlie結識的過程中,漸漸改變。
Willy Wonka的父親是一名牙科醫師,從小就非常注意Willy的口腔健康,限制Willy吃各種糖果。長大後的Willy心生一種「家人只會設限」的想法,因此脫離家庭追求自己想做的事,而創立巧克力工廠。家長只會叫你做這個做那個,不能做這個做那個等等,讓Willy對家庭存在意義產生懷疑。
Charlie寧可不要工廠也要與家人住在一起,讓孤傲的Willy第一次感到,家人可以是生命中最重要的。當我們不高興遇挫折時,家人是最好的聽眾與安慰。Willy在Charlie家中感受家庭成員帶來無可替代的溫暖,終於心生感悟,回到父親身邊,同時和Charlie共創未來。
本片以童話型式呈現,Johnny Depp的妝扮與談吐像極了神秘的魔術師,貫穿劇情前後,值得稱頌。想藉由Golden Tickets找尋工廠接班人、贈送工廠的Willy,卻因此獲得更多回報,重新肯定家庭的價值,恐怕是史料未及的。
改編自Roald Dahl著名的童話故事,「巧克力冒險工廠」捨棄一般電影的寫實風格,以創造一個神秘的童話世界為目標,讓觀眾悠遊於奇幻的巧克力工廠中,由Johnny Depp飾演的廠長Willy Wonka帶領,在神奇的工廠中展開冒險旅程。
好的童話故事能將教育內容嵌入故事情節中,在本片以五個抽到Golden Tickets的小孩,得以進入神秘工廠一探究竟為由,在參觀的過程中寓教於樂,算是適得其所。這五個小孩,有的很愛吃,有的被寵壞,有的很高傲,有的沉迷於科技世界,當然也有一個家雖貧窮卻珍惜家庭生活的小孩,名叫Charlie。從Charlie的爸媽及爺爺,為了實現Charlie夢想抽到Golden Ticket的願望而購買昂貴的Wonka巧克力,最後雖然失望而回,但知足的Charlie從不怨天尤人,可看出這三代人擠在一間小木屋中的溫暖與幸福。終於幸運之神降臨,Charlie抽到夢寐以求的Golden Ticket,得以和其他個性各異的四個小孩進入巧克力工廠內參觀。
既是童話,不能有人死亡。在奇怪的Willy Wonka帶領下,四個小孩分別因為個性上的缺失而出事,有的掉入巧克力池、有的變成大藍莓、有的掉入深淵、有的縮成姆指姑娘一般小,但這些孩子都不會致死,只是變成各種奇怪模樣作為懲罰。家長陪著孩子一起受罪,多少象徵著孩子的管教職責在於家長的意味。除了孩子之外,廠長Willy Wonka也在與Charlie結識的過程中,漸漸改變。
Willy Wonka的父親是一名牙科醫師,從小就非常注意Willy的口腔健康,限制Willy吃各種糖果。長大後的Willy心生一種「家人只會設限」的想法,因此脫離家庭追求自己想做的事,而創立巧克力工廠。家長只會叫你做這個做那個,不能做這個做那個等等,讓Willy對家庭存在意義產生懷疑。
Charlie寧可不要工廠也要與家人住在一起,讓孤傲的Willy第一次感到,家人可以是生命中最重要的。當我們不高興遇挫折時,家人是最好的聽眾與安慰。Willy在Charlie家中感受家庭成員帶來無可替代的溫暖,終於心生感悟,回到父親身邊,同時和Charlie共創未來。
本片以童話型式呈現,Johnny Depp的妝扮與談吐像極了神秘的魔術師,貫穿劇情前後,值得稱頌。想藉由Golden Tickets找尋工廠接班人、贈送工廠的Willy,卻因此獲得更多回報,重新肯定家庭的價值,恐怕是史料未及的。
「年輕的安徒生(中譯)」(Unge Andersen; Young Andersen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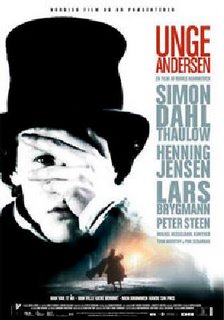 這是一部想像力奔放的丹麥電影,由曾得過金球獎的Rumle Hammerich執導,他擅長童話影片的製作,這是他的第三部作品,也是丹麥第一個有關世界童話家安徒生的傳記電影。
今年是安徒生誕生200週年,台灣少有紀念活動。安徒生童話你我小時候都讀過,許多耳熟能詳的童話,如醜小鴨、國王的新衣、拇指姑娘等都是他的著作。甚麼樣的人能夠寫作出那麼多傳頌世界的童話故事呢?安徒生天生就才華洋溢嗎?「年輕的安徒生」呈現他18歲左右的人生,讓觀眾一睹他從平凡轉而成名的重要關鍵。
安徒生成長於貧苦家庭,住在如狗窩般髒亂不堪的地方,卻擁有無法束縛的想像力。為了成名,他不斷拿著自己的劇本到劇院向公侯名流毛遂自薦,卻常吃閉門羹,受到眾人侮辱恥笑。這般的努力受到劇院經理Collin先生的注意,因欣賞他的才華而推薦到遠方學校就讀。該校校長Meisling是個博學而教學嚴峻的學者,對於安徒生天馬行空失去控制的想像力,決定以禁止他寫作的方式來遏止,企圖導正他的注意力於拉丁文等正常的科目中。
想像力過盛的安徒生,當然無法忍受校長這種作法,向Collin反應的結果,反而促使Collin與校長站在同一陣線。校長為了讓安徒生瞭解自己所作所為影響的不只是自己而已,採取「代替受罰」模式,只要安徒生犯錯,受罰的是他最好的朋友Tuk,Tuk也因此不斷受罰,頗有微詞。面對這種情況再也忍受不住的安徒生,決定離開學校,回到家鄉。
回到家鄉的他,雖然仍受到鄉親的歡迎,不過這與他對未來的理想仍有很大的差距。他決定再度回到學校,Tuk此時因病去世,Tuk的死亡對安徒生有很大的影響,他終於下定決心暫時放下筆與想像,好好地學習學校的基本學科,為未來的寫作打下重要的基礎。
兩百年前人類的壽命仍不長,年輕對成名來說是重要的時刻,錯過了這輩子就不要想成名了。藝術家的藝術天分,往往年輕時就可以看出,只是這樣的天分若沒有經過教育訓練來成型,可能只是放蕩不羈四處散射的思想,難以轉型成熟綻放偉大的光芒。本片拍攝手法呈現童話觀點,就像童話故事的結尾般,安徒生從此以後用功求學,為成為一個名作家而努力不懈,他的光芒再也掩蓋不住,終以童話創作稱頌於世界。
這是一部想像力奔放的丹麥電影,由曾得過金球獎的Rumle Hammerich執導,他擅長童話影片的製作,這是他的第三部作品,也是丹麥第一個有關世界童話家安徒生的傳記電影。
今年是安徒生誕生200週年,台灣少有紀念活動。安徒生童話你我小時候都讀過,許多耳熟能詳的童話,如醜小鴨、國王的新衣、拇指姑娘等都是他的著作。甚麼樣的人能夠寫作出那麼多傳頌世界的童話故事呢?安徒生天生就才華洋溢嗎?「年輕的安徒生」呈現他18歲左右的人生,讓觀眾一睹他從平凡轉而成名的重要關鍵。
安徒生成長於貧苦家庭,住在如狗窩般髒亂不堪的地方,卻擁有無法束縛的想像力。為了成名,他不斷拿著自己的劇本到劇院向公侯名流毛遂自薦,卻常吃閉門羹,受到眾人侮辱恥笑。這般的努力受到劇院經理Collin先生的注意,因欣賞他的才華而推薦到遠方學校就讀。該校校長Meisling是個博學而教學嚴峻的學者,對於安徒生天馬行空失去控制的想像力,決定以禁止他寫作的方式來遏止,企圖導正他的注意力於拉丁文等正常的科目中。
想像力過盛的安徒生,當然無法忍受校長這種作法,向Collin反應的結果,反而促使Collin與校長站在同一陣線。校長為了讓安徒生瞭解自己所作所為影響的不只是自己而已,採取「代替受罰」模式,只要安徒生犯錯,受罰的是他最好的朋友Tuk,Tuk也因此不斷受罰,頗有微詞。面對這種情況再也忍受不住的安徒生,決定離開學校,回到家鄉。
回到家鄉的他,雖然仍受到鄉親的歡迎,不過這與他對未來的理想仍有很大的差距。他決定再度回到學校,Tuk此時因病去世,Tuk的死亡對安徒生有很大的影響,他終於下定決心暫時放下筆與想像,好好地學習學校的基本學科,為未來的寫作打下重要的基礎。
兩百年前人類的壽命仍不長,年輕對成名來說是重要的時刻,錯過了這輩子就不要想成名了。藝術家的藝術天分,往往年輕時就可以看出,只是這樣的天分若沒有經過教育訓練來成型,可能只是放蕩不羈四處散射的思想,難以轉型成熟綻放偉大的光芒。本片拍攝手法呈現童話觀點,就像童話故事的結尾般,安徒生從此以後用功求學,為成為一個名作家而努力不懈,他的光芒再也掩蓋不住,終以童話創作稱頌於世界。
「機戰未來」(Stealth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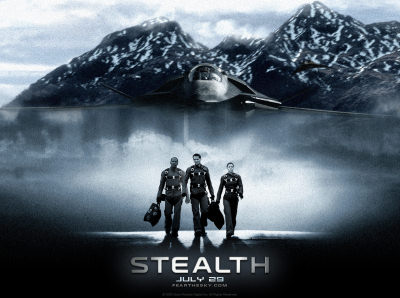 隨著資訊科技近20年來的突飛猛進,原本只存在幻想中的「機器人」,或由人類創造另一個行為、思想、概念類似人類的機器,漸漸成為可能。雖然以今日對人工智慧的瞭解來說,要創造理想中的機器人仍有非常遙遠的路要走,但我們已迫不及待想在電影中體驗這樣的世界,科幻電影中人造物具有智慧的片子不少,超前現實去探討未來世界的各種新問題。
隨著資訊科技近20年來的突飛猛進,原本只存在幻想中的「機器人」,或由人類創造另一個行為、思想、概念類似人類的機器,漸漸成為可能。雖然以今日對人工智慧的瞭解來說,要創造理想中的機器人仍有非常遙遠的路要走,但我們已迫不及待想在電影中體驗這樣的世界,科幻電影中人造物具有智慧的片子不少,超前現實去探討未來世界的各種新問題。
在「機戰未來」一片中,具有人類智慧的機器成了駕駛戰鬥機的「無人戰機」。美國海軍航空隊最優秀的三個飛官,被迫與無人戰機一起深入敵境執行任務。無人戰機的表現如何?人與機器能夠合作無間完成每一次任務嗎?
其實從近幾年的科幻片可看出,人們對充滿人工智慧機器的未來世界感到憂慮,描述機器人因智慧高而反抗人類的劇情頗多,多少代表我們對機器擁有智慧這種情況懷著高度戒心。機器應當以服務人類為目的,擁有智慧的機器更能夠滿足人們的需求,但過於聰明的機器是否會騎到人們頭上,尚未可知。只是我們是否應該事先防備?又或者最壞的情況是,人工智慧發展到極致,將成為人類滅絕的殺手?
片中的無人戰機,原是最佳秘密武器,不但飛行技術高超,彈著準確,因為無人駕駛就算被擊毀也無人傷亡。若聰明的「他」擁有完全的自主思考能力,會看得起人類嗎?會一直乖乖聽人類隊長的命令嗎?本片以戰鬥飛行員的角度,來呈現這類問題。
畢竟是電影,原本無視命令難以駕馭的無人戰機,當飛官實現承諾幫「他」撲滅機身上的火燄,救了「他」一命後,「他」終於懂得報恩,乖乖聽起話來。我想,這綜合了人類倫理觀念於智慧之中,「他」懂得有恩報恩的人之常情,因而不再一意孤行,只是這會不會太聰明了一點?甚至最後還自願以身殉難。當然,自殺式攻擊並沒有違背兩項基本準則,一是不落入敵手,二是完成任務。
人類近代文明的一項諷刺,在於尖端科技往往首次實現在殺人的武器上,似乎互相殘殺是人類最重視的事情。在這種慣性下,無人戰機也許將是人工智慧的第一個實踐。不論那個時代何時會來,技術以外的問題,可能才是必須優先解答的課題。
「童夢奇緣」(Wait' Til You're Older)
 香港電影有一段時間曾是華人電影的佼佼者,同時產生一股港星風潮。香港回歸中國,在日劇及韓劇文化入侵後,港片在民眾的心目中顯得沒落。不過偶有好的劇本造就佳作,像煙火短暫燦爛般點綴電影世界。「童夢奇緣」這部引入些許科幻情節的港片,在華人電影得獎風潮,一片武俠與藝術風裡獨創一格,以優美富含意義的劇情取勝,是蠻值得一探的港片。
香港電影有一段時間曾是華人電影的佼佼者,同時產生一股港星風潮。香港回歸中國,在日劇及韓劇文化入侵後,港片在民眾的心目中顯得沒落。不過偶有好的劇本造就佳作,像煙火短暫燦爛般點綴電影世界。「童夢奇緣」這部引入些許科幻情節的港片,在華人電影得獎風潮,一片武俠與藝術風裡獨創一格,以優美富含意義的劇情取勝,是蠻值得一探的港片。
卡司陣容皆是目前一時之選,劉德華的角色不再是打打殺殺,而是吃了秘藥一夜之間長大成人的12歲小男孩小光。當我們小時候,總是期盼快快長大,總認為身為大人可以不受約束,做自己想做的事,賺錢享用不必看父母臉色。小光認知現在他叫媽的人是他的後母(莫文蔚飾演),而這個後母可能是逼迫親生母親自殺的共犯,因此反抗心強,總是與後母作對,並盼望自己快點長大離開這個後母的家。這是本片一開始描述給觀眾得知的情況。
從神秘流浪漢提煉出快速成長藥水,讓小樹苗一夜長成大樹,也陰錯陽差讓小光一夜長成大人(劉德華飾演),劇情便充滿幻想,像是作夢一般。小光的夢想實現,他是大人了,收拾行囊離家去。在外流浪的日子,除了需借住同學家裡外,一切仍好。只是後來發生的事實竟像晴天霹靂般,推翻了他小時候的認知,這是劇情埋下的伏筆。一般外遇生子的情況,總是原配生的小孩年齡較大,外遇生的較小,因為我們認為與原配先生小孩是天經地義的。本片劇本利用這種盲點,讓先入為主的觀眾直覺認為小光是原配所生,因而同情小光的遭遇,算是精妙的一手安排。
發現事實的小光,才瞭解父母的偉大,只是神秘的藥效作用未曾停止,小光快速變老了。他的時間比任何人都短,快速成長也使得他將快速老化而死亡,並無解藥。浪子回頭想與父母重溫往日家庭和樂景況,卻已無法達成,小光父親(黃日華飾演)比小光年輕的鏡頭,深深震撼我們,因為總有一天將白髮人送黑髮人,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僅剩無幾。
人生只有一次,我們永遠不知道另一個選擇是否會比較好,結論是不論走的是哪一條路,只要安份在這條路上努力做到完美,即死而無憾。「吃碗內看碗外」,是一般人的通病,但常會造成一事無成的結果。小光盼望長大的夢想一夕實現,但實現後的他才知道當大人並不像以前想像那麼美好,此時想回頭卻已望塵莫及,因為人生只有一次。
劇尾的安排個人覺得有些草率,不過這也許是現實生活裡最好的結局了,其他部份請自行想像。人與人之間生命的交集常是片刻而已,何妨把握每個時刻,因為每個時刻都是悠久浩瀚的宇宙中獨一無二的時刻,想要從來不可能,想要複製也不可能。把握當下,是唯一的選擇。
「無米樂」紀錄片
 這部由台灣兩位記錄片導演花了15個月執導拍攝的「無米樂」,是少數能登上大螢幕與商業電影平起平坐的記錄片。當時是為了記錄台灣加入WTO對已近夕陽的稻作農業所造成的衝擊,拍攝地點在台南縣後壁鄉墨林村,這個在一望無際嘉南平原裡純樸的小村落中,以幾位年過60歲的老農民為主角,真實地記錄下一年之間,稻田從整地插秧,到成熟採收的種種歷程。
這部由台灣兩位記錄片導演花了15個月執導拍攝的「無米樂」,是少數能登上大螢幕與商業電影平起平坐的記錄片。當時是為了記錄台灣加入WTO對已近夕陽的稻作農業所造成的衝擊,拍攝地點在台南縣後壁鄉墨林村,這個在一望無際嘉南平原裡純樸的小村落中,以幾位年過60歲的老農民為主角,真實地記錄下一年之間,稻田從整地插秧,到成熟採收的種種歷程。
我們從來沒想到,幾位被認為「只會」種稻的七十歲老農夫婦,能有這麼深刻的人生哲理,這些哲理是經年累月累積而來的學問,比起我們這些在學校學習長大的「主流人生」來說,絲毫不遜色。
崑濱伯夫婦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幾位主角之一,年已75的他,喜歡唱歌,早年受日本教育,唱的都是日本歌,老一輩的人所擁有的日本記憶是我們不能忽略的。在片裡他真實地展現了種稻的辛苦,與承受不確定性結果的豁然態度。他說:「勞動不惜生命代價,彎腰插秧彎一整天,骨頭一直賣,所以農人是在賣骨頭。」他體會到農人勞動就像是在賣骨頭一般,這是我們無法想像的。他的老伴雖然像平凡人一樣喜歡「碎碎唸」,但崑濱伯與太太相處的方式很特別,以鬥嘴的方式來溝通,以詼諧的語言來化解衝突,這讓我們都自嘆不如。他是真正樂天知命的健康老農,向我們展現了農民看天吃飯的無奈,卻無法反抗。誰能夠反抗天?因此他認為,種田像修行,修行像坐禪一樣,控制自己要反抗天的怒氣,要抑制自己不要反抗。這是農民的寫照,因為老天爺太強大了,反抗也沒有用,透露出農民普遍無奈與認命的人生態度。
別看崑濱伯好像只會種稻,他對於台灣農業歷史的熟悉令人刮目相看。從「台灣光復」後國民政府來台,三七五減租、耕地放領、耕者有其田的政策,不是從教科書中學到的一言堂觀點,而是以農民身份的親身經歷,再真實也不過了。他能夠娓娓道來當時農民稻作被優先徵收為軍餉的情況,也能分析這些政策對地主與佃農的不同觀感,如地主恨死了「賊仔誠」,而佃農則感謝「賊仔誠」讓他們有機會翻身。此外,他對二二八事件政府殺害許多台籍菁英,導致後來台灣農民對政治的漠視也有獨到見解。我們在課堂中學習死知識,他則在生活中體會活學問。
其他如煌明伯、文林伯的現身說法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。從片中我們深深體認到,現在上班族做一天事領一天薪水是多麼得腳踏實地,這卻不是很平常的情況。農民每期稻作從整地到收成的好幾個月,只能在收成那一刻領那麼一次「薪水」,而這個薪水多寡還無法預知,甚至只要其間一個環節老天爺不賞臉,所有辛苦可能化為烏有,一切辛勞將無所回饋。這是台灣廣大的上班族無法體會的,卻又真真實實地存在。
「心情放輕鬆,不要想太多,這叫做無米樂啦!」樂天知命的農民,對生活下了注腳。農民對台灣經濟貢獻卓越,雖然WTO對本地農產品帶來衝擊,政府都不應該過河拆橋,坐視不管。究竟這一代稻農是崑濱伯口中的「末代稻農」,還是崑濱嬸口中的「末代滅農」,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課題。
 Sophie Marceau的美,不在年輕,而在神韻。在這部法國驚悚懸疑片中,Sophie飾演美女Chiara,為抓到洗錢高手Anthony Zimmer以身為餌。Anthony Zimmer據說時常易容變身,沒有人看過他的真面目,Chiara是他最愛的女孩,法國警察Akerman於是想利用Chiara誘捕Anthony。
懸疑片之所以懸疑,在於劇情進行中只揭露一部份的事實,故意隱藏了真相。其貌不揚的Francois,以夫妻不合獨自出外旅行的姿態出現在火車裡,Chiara看上了他,一付找人陪伴的有錢貴婦模樣,讓Francois體驗到富有的生活。其實Chiara把Francois識為Anthony Zimmer,因此故意接近他。
之後Francois陷入被追殺的危機中。這樣子的開場,Francois像一個無端惹來殺身之禍的無辜民眾,Chiara也對他感到抱歉,只得安排他到安全的地方小住。
不過Francois不甘處於被保護的角色,因為他愛上Chiara,他想要保護身為誘餌的Chiara的安全。
一切是那麼合理,只是Anthony Zimmer還未現身,不知身在何處。根據線報,警方在Anthony可能出現的山中豪宅中,佈署重兵包圍,Chiara再度身負重任,隻身深入豪宅一探究竟。劇情的詭譎在此,Francois偷進豪宅想維護Chiara的安全,同時Anthony Zimmer也進入了豪宅。到底Anthony的廬山真面目為何,觀眾與我一樣都急迫地想要看到。
當發現誤認Francois為Anthony後,警方及Chiara一方面會產生愧疚心態,另一方面有任何新線索都不再懷疑他,對他的判斷自然有失正確。這樣的心理伴隨著觀眾,當Francois在Chiara耳邊說出真相時,勢必跟Chiara一樣驚奇不已。真有眾裡尋她千百渡,伊人卻在燈火欄跚處的感嘆。大膽的Anthony Zimmer做出正確的判斷,Chiara最終並沒有把真相告知警方,Anthony仍舊來無影去無蹤,仍舊沒有人看過他的真面目。本片是警察捉強盜,但重點不在正義的實現,而在你來我往的鬥智,虛實之間的巧妙安排,畢竟片中沒有強調洗錢高手做了甚麼壞事。
設計他人的人反被設計,道高一尺魔高一丈,看得觀眾眼花撩亂。計計之中真假難辨,誰被耍了?是的,法國警方被耍了,但觀眾才真正被耍得團團轉。
Sophie Marceau的美,不在年輕,而在神韻。在這部法國驚悚懸疑片中,Sophie飾演美女Chiara,為抓到洗錢高手Anthony Zimmer以身為餌。Anthony Zimmer據說時常易容變身,沒有人看過他的真面目,Chiara是他最愛的女孩,法國警察Akerman於是想利用Chiara誘捕Anthony。
懸疑片之所以懸疑,在於劇情進行中只揭露一部份的事實,故意隱藏了真相。其貌不揚的Francois,以夫妻不合獨自出外旅行的姿態出現在火車裡,Chiara看上了他,一付找人陪伴的有錢貴婦模樣,讓Francois體驗到富有的生活。其實Chiara把Francois識為Anthony Zimmer,因此故意接近他。
之後Francois陷入被追殺的危機中。這樣子的開場,Francois像一個無端惹來殺身之禍的無辜民眾,Chiara也對他感到抱歉,只得安排他到安全的地方小住。
不過Francois不甘處於被保護的角色,因為他愛上Chiara,他想要保護身為誘餌的Chiara的安全。
一切是那麼合理,只是Anthony Zimmer還未現身,不知身在何處。根據線報,警方在Anthony可能出現的山中豪宅中,佈署重兵包圍,Chiara再度身負重任,隻身深入豪宅一探究竟。劇情的詭譎在此,Francois偷進豪宅想維護Chiara的安全,同時Anthony Zimmer也進入了豪宅。到底Anthony的廬山真面目為何,觀眾與我一樣都急迫地想要看到。
當發現誤認Francois為Anthony後,警方及Chiara一方面會產生愧疚心態,另一方面有任何新線索都不再懷疑他,對他的判斷自然有失正確。這樣的心理伴隨著觀眾,當Francois在Chiara耳邊說出真相時,勢必跟Chiara一樣驚奇不已。真有眾裡尋她千百渡,伊人卻在燈火欄跚處的感嘆。大膽的Anthony Zimmer做出正確的判斷,Chiara最終並沒有把真相告知警方,Anthony仍舊來無影去無蹤,仍舊沒有人看過他的真面目。本片是警察捉強盜,但重點不在正義的實現,而在你來我往的鬥智,虛實之間的巧妙安排,畢竟片中沒有強調洗錢高手做了甚麼壞事。
設計他人的人反被設計,道高一尺魔高一丈,看得觀眾眼花撩亂。計計之中真假難辨,誰被耍了?是的,法國警方被耍了,但觀眾才真正被耍得團團轉。